
丁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在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学科的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和持久的影响。
丁村是建国后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独自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此前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尽管因为周口店遗址及相关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而声名鹊起,但在中国所发现的遗址屈指可数,材料十分有限,对这一区域远古历史还只能是管中窥豹。丁村遗址群出土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使得神州大地上人类演化历史的重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该遗址给了中国学者独自开展科考工作、证明自己研究能力的契机。以前包括周口店、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等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或由西方学者操刀,或由西方人主持。裴文中、贾兰坡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奠基者,也是在西方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下工作。丁村的考古工作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承担,裴文中和贾兰坡亲临现场,主持发掘与研究,及时出版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裴文中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58),开启了该遗址长期发掘与研究的先河,也带动了日后在山西乃至全国范围的许多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60年间,丁村遗址新的发现层出不穷,研究逐步深入,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丁村遗址群的材料与成果对构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起到关键的作用。裴文中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将来自泥河湾的一件石制品和周口店第13地点的石器遗存作为“最早的人工制作的迹象”,将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早段”,将周口店第15地点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将“河套文化”定位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将山顶洞文化界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最早雏形。1948年裴文中将其修订为:早期为周口店第13、1、15地点,中期以“河套文化”中的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代表,晚期为山顶洞遗址。随着丁村遗址的面世,裴老在1965年发表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一文中,将中国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包括将周口店第15地点列为中期遗址),但基本框架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丁村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链接点。
丁村遗址对构筑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体系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个舶来的学科,在起步阶段难免对西方的学术体系照单接收。丁村的文化遗存被发现后,裴老等很快发现它和欧洲的石器类型与技术有很大区别,尝试摒弃照搬欧洲石器类型学,为建立符合中国材料特点的类型学进行探索:将丁村的石器划分为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大类,在大类之下又定名了“球状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厚尖状器(三棱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和“小尖状器”等。这样的分类更多依据器物的形态特征,而疏远传统上以人为判断的功能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应该说更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裴老等还发现丁村的石制品不但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迥异,与当时已发现的周口店、水洞沟、萨拉乌苏等遗址的出土标本皆有不同,于是将其命名为“丁村文化”,并开始思考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贾老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华北存在两大并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假说,并将其中的大型工具传统定名为“匼河—丁村系”。在对丁村石制品的分析中,研究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片和使用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碰砧法”、“使用石片”等概念,这对以后我国实验考古学的发展和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者还注意到古人类在该遗址广泛使用角页岩作为石器的原料,而这种材料的特殊性与丁村独特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也使日后学术界更加关注原料对石器技术与类型、形态的影响。这些成果与影响,使丁村成为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丁村遗址的发现推动了对中国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当初水洞沟遗址被发现时学术界对其与欧洲石叶体系存在关联的认知和对周口店北京猿人独特的本土文化的认识不同,丁村的石制品使中外学人产生了长久的争论,对该遗址是否存在预制石核程序和系统规范的剥片技术,是否存在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学术界莫衷一是。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丁村遗址出土手斧,表明远古东、西方人群间曾经发生过迁徙与文化交流。中国也有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件手斧出自丁村,并以丁村的材料为基础提出汾渭地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富集的三大区域之一。对丁村手斧的争议,发端于一件特殊的标本(P.1889),在原始报告中被称为“似‘手斧’石器”。其实该标本与丁村遗址、“丁村文化”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是从丁村东约5公里的沙女沟的地面上捡到的。丁村遗址的原始发掘报告对此作了清楚的交代,但有的学者或许不明就里,误将其当成丁村遗址的出土物乃至代表性的器型,直至今天还在此问题上继续引申和发挥。
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巩固了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多学科交叉与协作的传统。这一传统源于周口店遗址的科考工作,化石人类学、考古学、脊椎动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皆参与其间。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未被否定并得以维持和发展,丁村功不可没。因为遗址出土了人类化石、石制品、软体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研究时这几个领域的专家便顺理成章参与进来。又由于遗址埋藏于黄土和河流相砂砾层中,地质学家和年代学家也卷入其中。一些石制品受到磨蚀,表明一定程度的搬运和再埋藏,于是埋藏学也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这样,多学科协作便由舶来品变成我们自己的研究传统,在元谋、大荔、金牛山等很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被发扬光大。
丁村遗址还对新中国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该遗址由贾兰坡、裴文中先生主持发掘与研究,包括吴新智、邱中郎、王建、吕遵谔、张森水等很多第二代学人参加了发掘工作和后续研究,他们又继续指导学生和后辈学人在此学习和工作。作者本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被导师张森水先生安排到丁村遗址做发掘实习,与李占扬兄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个月,打下了旧石器考古的田野基础并初步掌握了对石制品的分类、测量和分析的技能。如今,王建先生的公子王益人兄仍在遗址挥洒汗水,延续学科的血脉。
当然,当年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不是尽善尽美。由于是配合基本建设,也由于工作点多,发掘面积大,发掘方法粗放、急躁,摒弃周口店时期建立的精耕细作的传统。没能对遗物的位置和埋藏情况给予足够的关注,野外记录也不如周口店那样详细、完备,在发表的发掘报告中,野外工作仅用半页纸寥寥带过,未能提供翔实的信息。这其中的缘由已无从探究,但事实证明这种粗犷的发掘方法存在许多问题,也与国际上先进的发掘方法和理念背道而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才在野外发掘和标本、信息获取方面重新与西方接轨。
另外,发掘报告和后续研究文章效仿古生物学研究中选择“模式标本”的范式,只选取少量“典型标本”加以描述和研究,未能提供更全面、客观的材料与数据,以致很长时期内人们误认为“丁村文化”是以大型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等为主导,碰砧法为古人类在该遗址的主要剥片方法,无法对其文化面貌获得全面、合理的认识,也使贾老的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假说陷入误区。类似的做法,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然,这是后人站在先哲的肩膀上所做的观察与思考,并不意味着对前辈的丰功伟绩和滋养了学科发展的丁村这方热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的否定。
标签: 考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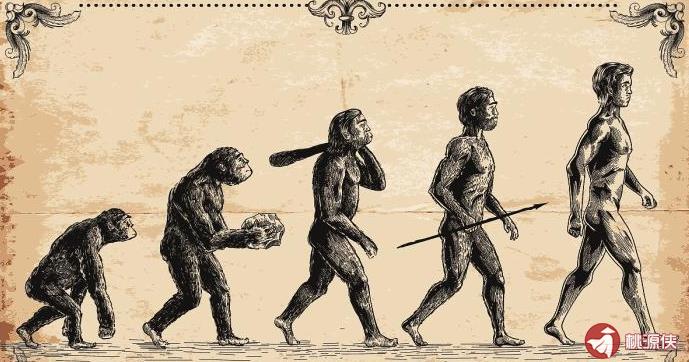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